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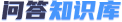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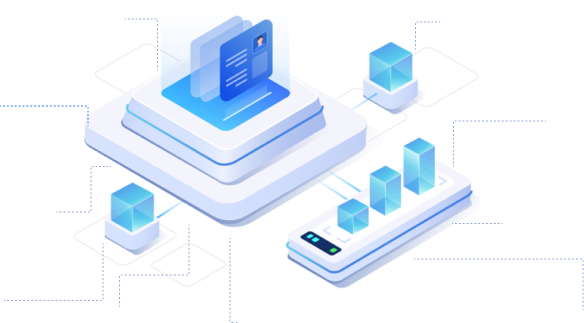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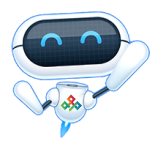 hi,我是小鲁,您的al服务专员,请选择您想要的服务~
hi,我是小鲁,您的al服务专员,请选择您想要的服务~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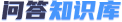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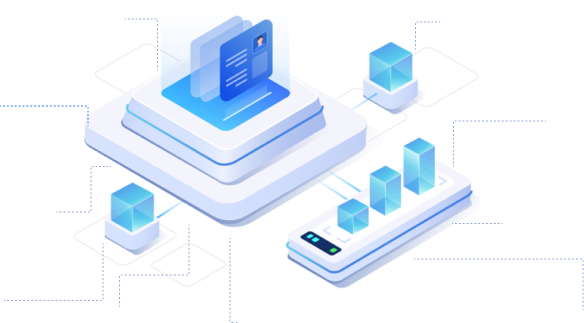
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,文化振兴作为“五大振兴”之一,正日益凸显其基础性、战略性地位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,并强调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,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,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”,要“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”工作,进一步激活乡村文化资源。这一系列文件明确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:文化振兴不仅是乡村发展的“软实力”,更是乡村重塑的“硬支撑”。
文化振兴战略下的“新农人”担当
青年“新农人”不仅是“文化振兴”的积极参与者,还是乡村多维转型的关键力量。他们的角色已远远超越了“返乡创业者”或“新型农民”的狭义定义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是数字化赋能的引领者。青年“新农人”具备较强的数字技术素养,能熟练运用短视频、电商平台、数字农业工具等,帮助农村实现“从田间地头到云端销售”的观念转变、产业升级。他们可以应用大数据、物联网、无人机、ai种植助手,提高农业生产效率,推进“智慧农业”建设。“新农人计划”“数字农场”等平台背后的青年创业者,改变了传统农业的销售半径与利润结构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是乡村产业融合的推动者。青年新农人善于跨界创新,能够打通农业 文旅 电商 文创的融合链条,推动产业融合发展。如将农产品包装为“文化ip”、将村庄节庆转化为旅游资源、将非遗技艺开发成文创产品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是乡村治理创新的参与者。青年“新农人”普遍具备较强的公共服务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,能够参与和推动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乡村治理体系。他们能以“数字工具 社群组织”形式参与村庄议事、乡村建设、公益协作。比如建设村庄公众号、协助建立“乡村议事会”新机制、参与乡村志愿服务和文化节筹办。
此外,青年“新农人”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、农村教育与社会服务的补位者、塑造乡土认同的文化中介人,他们身上的独特素养,不仅能激活乡村文化基因,也能重塑乡村青年群体的身份标签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先行力量,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,而是兼具振兴乡村情怀、数字技术素养、市场意识与文化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。他们不仅“下得去”“留得住”,更关键的是“干得好”“带得动”,是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由“沉睡”走向“觉醒”的关键力量。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乡村文化表达,通过产业融合拓展文化价值空间,通过内容创新增强乡村文化传播力,青年“新农人”正逐渐成为激活乡村文化基因、传承与创新地域文明的新生力量。
理论上,青年“新农人”可以被视为“乡村文化再生产”的新生群体。他们作为文化创意的实践者、传播者与文化产业运营者,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、可消费、可传播的新型文化产品,进而构建起“文化资本—社群动员—产业赋能”的乡村振兴路径。这一逻辑契合皮埃尔·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转换的理论,也与“新乡贤治理”理念形成互补,为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与文化建设新格局提供了实践支撑。
以创意助农催化乡村文化转化
青年新农人能够在乡村振兴中逐渐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,首先在于他们善于利用数字化平台助力文化转化,做到了从“守着金山过穷日子”到“触网即兴”的观念变革。当前,短视频、电商直播、微短剧等新媒介平台,已成为青年“新农人”连接城乡、表达文化、传播产品的重要工具载体。以一些电商直播、短视频平台的“乡村计划”为例,平台上涌现出大量来自乡村的内容创作者,他们用镜头记录非遗技艺、传统节庆、乡土饮食、村舍改造,以极高的审美风格创造性地美化了乡土俗事俗物,不仅为村庄赢得关注,也构建起了新的乡村叙事空间。
在直播、短视频等平台,很多博主以地域美食、非遗技艺、地域文化为基点,以农村家庭、乡土景观为视频呈现空间,积累了很多粉丝群体,带动了当地文创销售和旅游开发,形成“文化表达—流量聚集—产业转化”的闭环模式。这类案例表明,乡村文化并非“自说自话”,还可以通过新媒介完成转译,并有效地嵌入现代传播生态中去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的数字技术能力恰恰解决了长期困扰乡村文化发展的“数字鸿沟”问题。通过视频拍摄、社交传播、跨界协作等方式,他们将“隐形”的文化资源转化为“可见”的文化品牌资产,使乡村从“被看见”走向“被理解”与“被认同”,这不仅是文化传播,更是文化自信的建构过程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还善于使用“文旅 ”融合模式,催生文化“场景”,做到了从“看文化”到“用文化”。青年“新农人”通过“文旅 农业”“文旅 非遗”“文旅 生态”等多元融合路径,将静态文化资源嵌入动态消费场景,增强了乡村文化的体验感与市场价值。这些活动大多由青年主导策划、运营,将地方民俗、乡村风情与城市游客消费需求紧密对接,既实现了经济效益,又提升了文化影响力。青年“新农人”正通过创新“场景营造”,实现从“文化资源拥有者”到“文化价值创造者”的角色跃迁。
此外,青年“新农人”的返乡创业,也催生了“文化合伙人”,做到了从“独角戏”到“共创局”。乡村文化振兴不能只依靠少数“能人”,更需构建良性共创生态。近年来,多地尝试通过“青年返乡合伙人”机制,推动青年与村集体、新乡贤、村民合作,组建文化发展合作社或文化企业,实现“资源共享、品牌共建、收益共赢”。地方政府鼓励青年与村民共同成立文化合作社,青年负责运营与传播,村民负责生产与传承,一起打造民宿、非遗文创、农耕体验、乡土美食等产品。通过“合伙人”机制,青年不仅成为文化项目的策划者,更是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参与者,形成稳定的文化振兴共同体。
构建新形态引领乡村文化基因的现代重塑
青年“新农人”之所以能激活乡村文化基因,不仅因为其掌握新工具与新思维,更因为他们具有“跨界融合、连接城乡、共创共享”的价值理念。他们不只是“农民”,更是“文化创客”“数字传播者”“乡村运营者”,正推动乡村文化生态从“自发式传承”迈向“系统性重塑”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的文化产业运行模式可以推动乡村文化“生态系统化”,因此需要实现跨部门协同与政策保障相结合。当前,青年参与乡村文化创新面临政策碎片化、资源分配不均、平台支持不连续等问题。为此,需构建起涵盖文化、教育、科技、农业、旅游等多部门协同的文化振兴政策体系,鼓励青年深度参与乡村文化建设。
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,“加强乡土文化能人扶持”,应在此基础上,出台青年乡村文化创业扶持计划,包括资金支持、创业指导、文化场所赋能、内容孵化机制等,推动青年“新农人”由“个体探索”走向“系统支持”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要全面发挥其主体性作用,需要完善“文化新基建”建设,推动文化数字化、平台化、网络化发展。乡村文化要实现“现代表达”,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机制的支持。应加快推进乡村“文化新基建”,包括文化数字资源库建设、乡村文化数据平台开发、数字乡建人才培训等。通过打造一批“数字乡村文化样板村”,推动乡村文化内容创作、传播与管理的数字化转型。如利用ai、大数据等技术对地方方言、民俗影像、老物件等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整理与在线呈现,这一措施不仅有助于文化保护,也能成为教育、旅游、传媒等领域的内容资源。让青年“新农人”在“新基建”中成为平台管理员、数据分析者和内容创造者,提升其职业认同与文化价值感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助力乡村振兴,更需要形成“乡村文化共同体”,多部门、多渠道、多维度打造具有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的乡土网络。青年“新农人”的文化实践,最终目标是构建起一个“既有在地性也有流动性”的文化共同体。这种共同体既扎根于乡土情感,也链接于外部认同,是一种“多向互动、情感共鸣、价值共建”的文化网络。要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、青年协会、乡贤理事会等基层组织作用,形成“以文化人、以文润村”的社区机制,让文化成为乡村治理的新纽带。
同时,应鼓励建立“返乡青年联盟”“数字文化合作社”“乡村文化传播平台”等新型社群,推动“创作者—村民—游客—消费者”的多元互动关系,使乡村文化从被动供给转向主动生产,从“标签化展演”转向“个性化表达”,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与文化现代化。
青年“新农人”正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姿态与文化意识,重构乡村文化的表达方式、传播路径与产业逻辑。他们不仅是乡村文化的讲述者、传播者,更是文化基因的激活者、文化现代化的引路人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,青年“新农人”理应被看见、被支持、被赋能,成为中国乡村文化繁荣与再生的中坚力量。